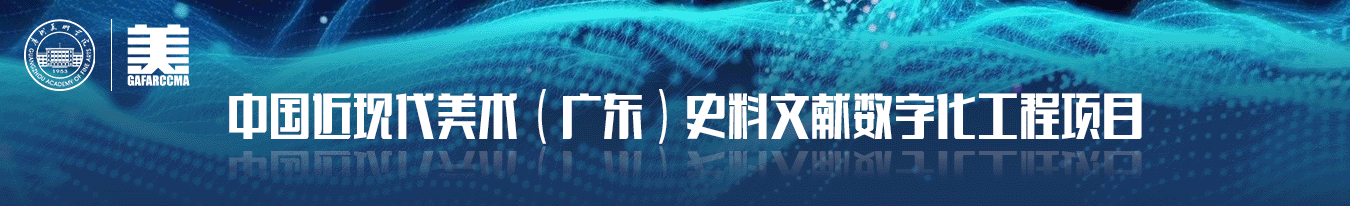在逃难中学习美术
我小时候学画,主要是从6岁,我父亲参加国民党军队,去抗日了。我跟我母亲两个人就逃难到香港,到了香港就没钱生活,更加没钱去读书了,我母亲就去做点小买卖。最苦的时候,讲起来真的很惨。在香港没钱,偶尔靠一些亲戚帮忙,但是你总不能靠人家。所以有一天(我这个印象也很深),我母亲带着我跑到九龙,我们住在香港九龙那边……那里有一个难民营,我母亲想带我去难民营,进难民营有得吃。但是一看就觉得好惨。我跟我母亲两个坐在那里看了整整一天,看那里面怎么样,原来打架、抢吃的东西,有些在太阳底下坐着杀虱子,都是跳蚤,很悲惨的。我母亲不敢进去,思想斗争了一天,坐在那里不敢进去,就带着我回来。 那时候没有得读书,什么事都没得干,我母亲就买了一些纸,一些笔教我学写字,她怕我荒废了学业。我那时6岁已经读到二年级了。后来再没事,就拿着瓦片在地上画画,从香港过海的轮船,有军舰,那时候很讲究军舰是什么特点,轮船是什么特点,就在地上画。再画香港好多新型的汽车,各种汽车,流线型汽车,双重巴士全都画,画完又画飞机。看小人书,就画文武生、花旦,这些随便就会画出来,也有点样子的。从那个时候开始,毕业到了智瑞(音)中学附小学校,就是受爱国主义教育最深的那个学校,那些比我高年级的同学,写很多美术字,也很吸引我……我总在那里看,各种各样的美术字我都学了。所以小学四年级以前,各种美术字我都会写。最后五年级补上一课,学了仿宋。从那些地方就学,后来又知道什么叫做写生,就是老师教的。 希冀国家富强
总是有一个思想,希望国家富强,希望国家真的快点强壮起来,壮大起来,不要给人家欺负了。这种愿望从八九岁的时候,就已经建立起来了。最典型的(是)我跟两个小朋友,因为我那个时候喜欢美术字,才十岁左右,有两个小朋友加上我三个人,我在每人的这个地方写了“抗日”两个字。三个小朋友偷偷地写,回到家里拿一个针刺,就相当于纹身。现在还留下一个红斑在这里。就是因为这段经历激发了(我)坚决要跟日本人抵抗。后来给家里人发现了,他说如果你给日本人抓到了,连命都没有了,硬是把这两个字刷掉,现在留下一个红斑,就有一点点红在这里。 日本投降了,就回家乡……逃难就逃了七年,回到家乡的时候,那个心情真是很难形容,觉得每一个地方都可爱。每个地方都好像很亲切,非常宝贵。以前在日本人的手上,现在又回来了,多高兴,那种心情真的很难形容。 在华南文艺学院学习雕塑
(选择专业时)确实有个现实问题,经济没有来源,我父亲去坐牢,我母亲自己都顾不了,怎么可能有钱给我呢。我想经济条件那么差,算了不考油画了。我最喜欢油画和雕塑两样,雕塑、油画我都觉得有种神秘的感觉,是怎么搞出来的呢?总有一种神秘的感觉。雕塑也是,怎么能够做出来的呢?因为学雕塑不用钱,石膏粉是学校给的,泥巴不用钱。学油画就不得了,要好多钱。没钱。我在文艺学院的时候,其他同学都有一个水彩画箱,我都没钱买,就拿个画板去画水彩。人家都是有个水彩画箱,里面放颜色什么东西的,我没有。那个时候经济比较艰难一点,所以选了雕塑。 其实在文艺学院学雕塑时间很短,非常短,老师没有讲过怎么做,都没有教过,都是摸着做,看着人家这样做,我就这样做。但是有一条,那时候老师讲了一条要看边线,那是法国的方法。跟苏联的方法不一样,苏联的是从结构出发,从空间感觉出发。我们那个时候老是找边线,等于中国画里面讲的山行步步移,就是每转一点又不一样,转一点又不一样,所有的边线组成就是一个整体的,是这样的一个观念,也不能说是最好的方法。 木料的来源 我一共创作过两件木雕,一件是《珠江岸边》,一件是《水乡女民兵》,两件都被中国美术馆收藏了。 《珠江岸边》用的是楠木。楠木是很珍贵的一种木料,故宫维修的时候换下来的旧木头,不会变形。我们去得晚,木头几乎被其他学校买光了,我们学校才去买,买的一些都是很小块的。我这么大一个木雕,差不多用十块木头拼起来。不过也好,我跟一个木工师傅学会了怎么拼木头,拼得很好,拼得很舒服。后来那件(《水乡女民兵》)就不同了,学校给我30块钱向木雕家具厂去买木头。木头是一块多一斤,那块木头重105斤,一共要130多块钱。我说我没有钱的,学校才给我30块,我到哪里找100多块钱去买你这个木头呢。那工厂也很好说话,说这块算次品,29.9块卖给了我。 做雕塑是“不择手段”的
(1957年李汉仪与雕塑系教师同赴龙门、云冈考察古代雕塑)这一段生活我印象也很深。因为到现在都没人知道,没有给介绍出去。去龙门我们第一站是去巩县,去看礼佛图。到了巩县,我们借一个中学的教室午睡,午睡一起来,整个县城都淹了,去不了了,就马上去了龙门。
文化部曾派人去(龙门石窟)翻了一批雕塑,使得研究所很有意见。因为做这批翻模的时候损坏了原作,他们敲,很凶地敲,因为石膏抠得很紧。(研究所)就很有意见,以后不准翻。糟糕了,那我们想翻怎么办呢?他说不准翻就是不准翻,他是权威了。后来我们想了一个办法,用泥来做外模。石膏咬得很紧,要撬,泥巴是软的,永远伤不了石头。我们开始做这么大一块浮雕压下去,把那个模拿出来就可以翻一个了。我们就是跟那个研究所商量了,我们这样行不行呢?他说这样好像还有点道理,还可以、还可以,让我们翻了。 ……后来我们发现,要合模的时候,一翻出来就有一条缝,那条缝有时候比较宽,怎么办呢?我们在拼模的时候,把泥模拼起来的时候,把那些缝填了它。一填又不一样的,填下去的地方是滑的。因为那些石头经过多年的风化,都有一点点斑点之类的,它没有那个东西。我们想这样不行,就捡一些当地的石头,压压压,压回那些小起伏,跟原作一模一样了。 后来发展到什么呢?这个讲故事了,李祥美跟王福臻两个人。国庆十周年的时候,他去做雕塑,做了李闯王。他看到我们在翻模的时候,用石头印,效果蛮好,他做李闯王的时候也用石头印,那种特别的效果。潘鹤都看到了,所以他的《罢工》下面都是石头印的。这个就是技术、工具的变化,其实做雕塑是“不择手段”的,(或者说)择一切手段,好多都是偶然发现的。
|